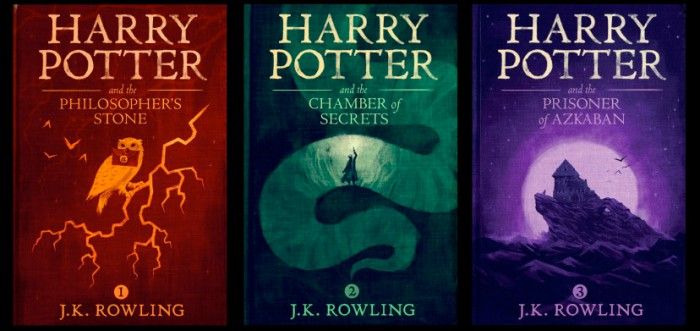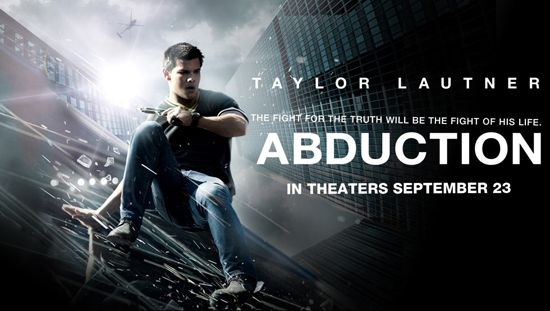我看见 蟑螂的暮光 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接下来的27年里反复思考它。我仍然考虑。我不记得我在哪里看过吉田裕明(Hiroaki Yoshida)的那部美丽而又怪异的昆虫人戏,而且带我进行粗略互联网搜索的母亲也没有透露1991年在罗克西(Roxie)演出,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看到它在那里。 Roxie既小又黑,所以靠近我们看到它明亮通风的地方。 (如果您正在阅读此书,并且知道它在哪里播放,请伸手去拿。)电影不轻而通风。这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空间,隧道,油腻,充满面包屑的角落的电影,里面包裹着一叠起皱缩的薯条。
我非常喜欢它,但这不是最好的电影。邪教经典的方式很好:它们中的某些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引起观众的共鸣,但是关于它们的某些东西却使它们不受欢迎。它们通常太多或太少,太慢或太快,太激烈或太平淡,太原始或太原始了,它们并不适合所有人,并且通常不完美,但它们会突出。生活也是这样,或者至少我的生活是这样:它是健康地发生和开始的,很少以我想要的速度或温度发生。但是像蟑螂一样,它仍然存在。据说蟑螂会在核启示中幸存下来。我不会。但是只要我在附近,我就会继续回到这部电影,并尝试找出原因。一些有关 蟑螂的暮光 早起并留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界的变化,它积累了新的意义和层次。
一郎很诚实。汉斯很坚强。”用这些话,一个年长的蟑螂试图在电影的中心情节之一上为电影的温柔可爱的19岁主角内奥米(Naomi)提供咨询:一个年轻的蟑螂女人在社会混乱的时期被迫在两个求婚者之间进行选择。和真正的暴力动荡。在六岁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初生的浪漫观念,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三角恋时,我就理解了。这些词在其下面移动着一些部分–我以后将学到的是重力。我的胃不舒服,激动得令人不舒服,眼睛更加坚硬。赌注是模糊的,但我必须知道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我的注意力跨度已经很不错了-我说这并不是要强调任何早熟感,只是要注意我一直很想坐下来观看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线带我完成了电影的其余25分钟,当战争和种族灭绝的主题在齐藤单身汉的公寓附近撞上时,蟑螂人间战争的场景将杀死汉斯,一郎以及整个故事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其他每个人,除了在Naomi的身体里乱扔了一小撮蟑螂。
其他部分也很引人注目:娜奥米漂亮的翅膀,像披肩一样坐在她身后(我被她的美丽迷住了)。一郎(Ichiro)在这里过夜的皇冠牛奶巧克力包装纸(在食品包装中睡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趣)。斋藤(Saito)穿着他的汗衫时令人愉悦,他未来的女友将她的内衣挂在外面晾干(我正在看一些成年人的东西,我看到一些成年人可以看到的东西,虽然我不理解,但是很着迷,因为这意味着某些东西,不清楚的东西,私人的和个人的)。斋藤和他的女友再次在他们的公寓地板上吃百吉饼三明治,大规模杀人后(我们在家吃百吉饼,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我注意到,关于诚实和坚强的一句话立即浮出水面,形成了紧密的记忆结,多年来,这种记忆会越来越松动。
kevin o liarining aniq qiymati
在高中时,我和那些会成为明天书呆子看门人的人在一起,这意味着我喜欢动漫,但并没有太多谈论它–我担心真正的动漫迷会告诉我我错了。在大学里,我的自尊心得到了适度的衡量,足以谈论我的兴趣并迅速发现没有人听说过 蟑螂的暮光 。从字面上看,没有人。那是2000年代中期,也就是互联网的早期。我从未想过要在搜索栏中输入标题。取而代之的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在谈话中提出来,并总是遇到空白的表情。我不认为知道某些相对深奥的东西很酷。我开始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这是从一个有时混乱的童年开始的一种和平幻觉。所以我不再谈论它。一阵子。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花了一个小女孩金鱼把虫子带回来。我与当时的男友和最后的丈夫的第一次约会是对 小马 。电影放映后,我们回到我的公寓,谈论动漫。他很友善,没有为我说话或嘲笑事实:我很舒服,可以看蟑螂电影。
tanna tulkiga nima bo'ldi
“这是这部电影,蟑螂在打架,还有一个三角恋。”
“你的意思是 乔的公寓 ?
“不。叫做 蟑螂的暮光 “
“你的意思是 乔的公寓 。您正在描述的情节 乔的公寓 “
“不是!”
men jozibali ekanligimni qanday aytishim mumkin
他的固执让我更加努力地回到了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将在我们的整个关系中持续下去,一直持续到今天。就约翰·达尼尔(John Darnielle)而言,我们是双台高维护机器,而这些机器是我们痴迷的,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在脑海里嘎嘎作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张开嘴让它们出来
但是为什么 蟑螂的暮光 忍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已经看过几次了,但我仍然很喜欢它,尽管我的背景很不相同,但我最近在新奥尔良的奥杜邦蝴蝶园和昆虫科看到了一个展览,里面有假家中的真正蟑螂。 –文字虫子在规模化的厨房中爬行。我作呕,不得不走开。很抱歉,一郎,汉斯和娜奥米看到你被大眼睛,人类的表情和情感所吸引,这是一回事。关于Saito的意大利剩菜,您的酒宴会让人着迷,如何从一瓶酒中塞出软木塞并称出陈旧的意大利面也很有趣。我什至可以在说话的小草丛中找到魅力。而且我不明白,作为一年级的学生,斋藤先生会把你赶出去–他对这些生物如此残酷,只是想过着平静的生活,偶尔吃点意大利面就不吃零食了。
六岁那年,我没有自己的家,我妈妈照顾了罕见的蟑螂,这些蟑螂从我们公寓的水管中冒出来。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不喜欢蟑螂。我不想看到他们爬到我的下水道,我不想看到他们从垃圾袋里突然冒出来,我绝对不想看到他们在我家中玩耍。他们是屏幕上受欢迎的访客,但不是我的生活。
对于马达加斯加嘶嘶蟑螂,我是个例外。蟑螂的大小和外观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我第一次在明尼苏达州科学博物馆遇到了这些工作夏天。它们是昆虫世界中的大熊猫:移动缓慢且近乎平静,它们以近乎装饰艺术的方式颇具吸引力。它们是优质,低维护的宠物。大多数蟑螂都缺乏这种区别。但是大多数电影都不是 蟑螂的暮光 ,这会立即引起我的共鸣,而我通常会用卷起的杂志砸碎它们。尽管这部电影在真人和动画之间来回切换很尴尬,但这仍然是上下文和框架的力量,您会感受到与世界的社区感,这些世界沿着踢脚板,在吃饱了的蛋糕上腐朽的聚会以及在丝质内裤上沉睡着。在蟑螂社会中,世代相传和社会动荡不胜枚举:年长的一代担心年轻的一代,年轻的女性谈论对婚姻的恐惧,年轻的男性争取家庭的稳定或在战场上的荣耀。这些是人为主题,与那些随意地将其杀死的实际人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把曲线球推向了普遍接受的生物社会秩序,引发了关于我们如何对待最底层生物的潜在不舒服的问题。
我想强调一下潜在的问题–我毫无疑问地打开一罐Raid。尽管我生动地记得蟑螂进行战斗训练的场景,但当我一郎跳下,试图飞翔并失败时,我的心却跌落了起来,就像斋藤先生的女友一样,这丝毫没有引起我道德上的焦虑,这使Naomi的后代被遗忘了。更令人不舒服的是,这些主题从小就飞过我的头顶,但在以后的观看中却显得丑陋。我说的是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齐藤先生的女友不赞成他过快的生活方式,并发起灭绝运动,这会让任何害虫防治公司都为之骄傲:他们绑扎着看起来像经过改良的医院擦洗剂,然后喷雾,压榨和诱捕,把“粉碎物”带回来。 ,炭火和毫无意义的残害”,年长的蟑螂从与细野部落(Hosono)部落的战斗中回想起,细野部落占据了斋藤之前的公寓。对大屠杀和广岛的寓言并不微妙,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有人认为人类从伊甸园中驱赶蟑螂,并打算消灭它们,再加上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使该物种持续纯净。某一时刻,将军大喊:“……这种杀人的种族灭绝不会无休止。每杀死100人,我们将再繁殖10,000人!”
被打倒后,大量和虚假的纯血观念是重新出现的一种方法。适应和进化是另一回事。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第一个选择。这似乎是无害的,但如果冗长地回顾电影的话,第四句话就疯狂地变成了强有力的反犹太主义。出于出生原因(我有资格参加生育权旅行)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以及重视批判性思维的人,我努力采用第二种选择。这种努力扩展到了我爱的电影,我不欣赏T 蟑螂的曙光 就像我六岁时做的一样,但我也不会因为融入民族主义和优生学的主题而拒绝接受它。据说导演吉田裕明(Hiroaki Yoshida)可能一直在评论日本的贸易惯例,其现代decade废,富裕国家与西方的复杂关系。至少从我的文化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是混乱的:一方面,吉田拥护被边缘化的人。另一方面,处理这种状况的方法并不仅仅是克服残酷的坚持,而是接受可怕的死亡和对自己人民的不妥协的接受。有很多需要解压缩的东西,但是各层之间的跳动使它值得付出努力。通过了解电影时间的背景,时间的背景以及与当前价值的关系,电影可以在意识和对话中生存。 蟑螂的暮光 不再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东西,但它具有优点,质感和颠覆性,所有这些都在稍微笨拙的实景/动漫包中。
我的爱 蟑螂的暮光 始于一连串的图像和简单的感受。那爱之所以持久,是因为它发展了。真正的爱并不意味着保持时间定格,它随着思想和分析而增长,并因历史和成人情感而变得强大,这是一种可以承受厌恶女性的人,新纳粹博客和千分之一的热情。确定您不是指乔的公寓吗?”。它不仅可以克服负面影响:我看过几百部电影,这些电影比 蟑螂的暮色, 但它继续脱颖而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它,但是我相信它超越了怀旧。当然,它超出了饱和度(“您确定您不是指乔的公寓吗?”)。它不断回来,因为我能够清楚地思考它,用批判的眼光调和并增强了情感和兴趣。某一时刻,娜奥米的祖母在梦中来到她身边,以兔子玩具的形式出现,告诉她:“为了改善我们的繁殖……上帝给了人类致命的毒药。”这种达尔文式的逻辑,如果不是对我个人而言,而是在如何热爱娱乐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如果不能以不同的情境,年龄和新的信息对电影进行不同的欣赏,那么也许永远就不会被人们所钟爱。 。但是,如果零件得以生存,则通过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时代,它们可以以诚实和坚强的方式永远生存。